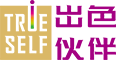本文转载自《人物》2019年8月20日,作者谢梦遥,编辑|金焰
平行世界
生为同性恋,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选择。那是你天生的样子。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可以走左边,也可以走右边。同样,身为同性恋者的母亲,也不是一个选择。
她们是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一代人。几乎鲜有例外,对于这些普遍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者更早的女性而言,在意识到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之前,同性恋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平行世界。「同性恋3个字,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离我太遥远了。」来自广东普宁的单亲妈妈贺荣桂说。错误观念大行其道,很多母亲还认为,那是西方社会某种闹着玩的时髦生活方式。
同龄人中不见出柜者,同性恋文学在她们接触到的范围里不存在。唯一的连接可能,大概是电影了。但即便看过含同性恋元素的电影,也不意味着什么。住在上海的妈妈朴春梅早年看过《喜宴》,对于里面男性间的接吻与拥抱,她没看懂,以为美国很开放,那不过是男孩间一种礼貌行为。
来自陕西网名「暖阳」的妈妈回忆,她曾买回《断背山》的影碟观看,被电影里恋人间的情感深深打动,但依据她当时的认识,同性恋是一种由特定环境造就的主观选择。看完电影,她的下一个举动就是将光碟藏在柜子里,「千万不能让儿子看见,要不跟着学怎么办。」
出柜需要勇气,需要明确的自我认同,需要反复的心理建设,也需要循序渐进的铺垫。孩子在出柜前,有意无意释放出来的信号,母亲们会选择性屏蔽。家住东北的张菊英曾去广州探望儿子,发现儿子和室友其实是住在同一间房,房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一条双人被。她感到不对劲,但马上自我劝慰,不要想太多。看到安全套,她只是想,大概是哪个孩子跟女生谈恋爱了。回东北那天,路上儿子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不该被歧视,才说几句她就堵回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
出柜一刻到来时,多数母亲第一反应不是痛苦,而是茫然。「妈妈,我是同志。」当儿子对她说出那句话,上海妈妈朴春梅感到莫名其妙,她想起儿子入了党,赶紧回答:「我也是。」
贺荣桂的女儿向她捅破那层窗户纸时,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作为单亲妈妈的她,一向强势,女儿自小到大,她骂的最多一句话是,「你比那个猪还笨还蠢!」但听到那一刻,她没有任何反应,目光还在屏幕上。于是女儿一遍又一遍地陈述那个事实。她缓缓转过脸,「嗯,我知道,我知道。」又转回去看电视。「妈妈,你怎么没反应呢?」她并不是真的看电视,她像是置身于无法接收也无法传递任何信号的盲区里。
一位来自贵阳的小学老师——她管自己叫「豪妈妈」,将成为贯穿这篇报道的主角。主角的故事会有更多巧合与戏剧性,但抛除这些,所有的母亲的心路历程是相似的。2018年7月,在同性恋这个词像外星飞船一样砸开她的世界的那个夜晚,豪妈妈经历了另外一场大哭。因为琐事和父亲争吵,家庭生活中积压多年的委屈全部涌现出来,几十年来她从未在父母面前哭过,那天竟哭了起来。
还是在长沙工作的儿子发来微信一通开导,让她情绪好转。儿子23岁,永远是那么贴心。话题转向别处,她问道:「过年回来吗?是不是应该可以给妈妈带个女朋友回来?」
「妈,可能我的想法和您不一样。」
「不可能要独身吧?」
「独身倒不会,」儿子说,「只是会找的人和你们的那种希望离得很远。」
「不可能找个离婚的吧。即使那样,只要是合得来,都可以。」她说。
「不是。」
「离婚带一个小孩的?」她觉得自己是个开明的母亲,常理来讲别人不能接受的情况,她能坦然讲出来。
「不是。」
「那你不可能找一个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吧。」猜谜游戏里的所有选项都试过了。「哎哟稀奇,你要找什么?」儿子不说话。
有个词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她脱口而出。似乎有那么一个瞬间,豪妈妈觉得她只是开玩笑。「难道你是同性恋?」
「不愧是我妈,太聪明了。」
过往像电影一样在脑海播放,那些曾被忽视的蛛丝马迹重新显现。
豪妈妈永远难忘儿子大学毕业后那半年时光。他没有找工作,假称考研,其实把心思都用在照顾母亲身上:每天7点就起床,变着花样地做早餐,下午买菜、打理家务,晚上一定要煲汤。「那半年我简直像过老佛爷的生活。」豪妈妈说。
现在,她对那半年的相处,有恍然大悟之感——儿子早早在为出柜做着铺垫。「他可能就是用这半年的时间,报答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对他的付出。」她猜想那大概是一场漫长而温柔的告别,儿子早就做好父母若极端抗拒,日后难再来往的准备。
她又想起,儿子找到工作后,离开贵阳前几天说起的一句话。「妈,我家奶奶把我爸害惨了,我爸也把我害惨了。」那句话说得很突兀,当时她没放在心上。现在她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他肯定早就知道他爸爸不一样。」
儿子是知道这一切的。当年她与丈夫才认识一个星期,婆婆就叫他们结婚。随着孩子长大,丈夫变得愈发奇怪,反感与她身体的触碰,有次她主动靠近,他一脚把她踹下床。「长期都是背对背的,到后来基本都是分床,手都难得碰一下。我守活寡守十几年了。」丈夫工作日都住单位,他们极少交流,出门遇见那些男同事,「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她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么多年来,却从来没有往其他角度想过。
事情是这样发展的:首先,她知道了自己有个同性恋的儿子。然后她想明白了,他爸爸和他是一样的人。结婚30年,她用了30年,终于抵达这一结论。

孤岛
初始的茫然过后,不同的感受会相继出现:震惊,恐惧,失望,忧虑,不解,自责,最终含混到一起。没有例外,以泪洗面是一定的。当母亲以为自己孩子是异类的时候,她们看不见彼此的时候,那感受就像在孤岛。
一位来自湖北孝感的谭姓母亲说,因重疾耽误高考,国企改革中她与丈夫双双下岗,被人骗走家里所有的十几万积蓄,所有这些磨难都未曾让她流过一滴眼泪,「女儿的出柜,却让我几乎流完了这辈子的眼泪。」
一个靠经营小超市将孩子拉扯大的湖南农村母亲,在两个儿子相继出柜后,丈夫抛弃她去找了别的女人。有几个晚上,她独自走在河边,想跳下去。「妈妈,你不能这样子。」大儿子在河边找到她,哭着说,「你要是走了,我和弟弟怎么办?」她嚎啕大哭。
相比父亲,母亲更容易成为被指责的那个人。自责成为一种普遍情绪。很多母亲会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把孩子生错了?」她们开始审视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环节,将那些无关的错误与疏忽揽到自己身上。「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吗?」「是我和他爸爸经常吵架,让他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吗?」
说出来,对孩子是某种解脱,但在母亲的世界观里,有如投下一枚核弹。那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亲子关系在废墟上重建的开始。这期间伴随着战争。张菊英每天给儿子发短信说服,前前后后发了有100多条。合肥妈妈朱丽珍经常跟踪儿子,在儿子站上天台威胁自杀后,她一天内打了3次110。警察管不了,她请求道:「要么你把我儿子拷走吧,他是个变态。」常州的杜姓妈妈为了逼女儿改回来,软硬兼施:拿剪刀扎自己的手,假称得了好几种病,还从网上下载心电图吓唬女儿。女儿屈服了,删掉了女友的微信。
那些在事后讲述中显得最轻描淡写的接纳,真实过程要艰难得多。
「妈妈,你爱不爱我?不管我是什么人,你都爱我吗?」10年前,被儿子这样问时,深圳妈妈董婉婉回答,「我爱你啊。」
「我是同性恋。」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对话至此结束。故事翻篇,她成了深圳最出名、最活跃的一位同志母亲。但她也承认,在独自消化所有信息的过程里,「想到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会走得很难」,她难过了很久。甚至在半年之后她还抱着幻想,让儿子找女朋友。
即便宣称接受了孩子,情绪还是会反复。那一线的隐秘念头,难以切断。朴春梅当初选择辞职来上海,就是为了走入儿子及他的伴侣的生活。3人住在一起,一切感觉很融洽,儿子隔三岔五会带同志圈内的朋友来家里吃饭。朴春梅暗自行动着。每次她都会选一个看上去最好说话的,假托来厨房帮忙,把门关上,抓紧时间问一堆问题,她总期待能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她,同性恋可以改。有次问到一个人,马上去美国读博士后了,「你学历这么高,为啥不努力,怎么还同性恋呢?」那人回答:「阿姨,我就是美国总统,我也是同性恋。」
孩子出柜,父母进柜。一位上海彭姓母亲,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家里的秘密。一次去公园,她听到两个嗑瓜子的女人议论同性恋恶心,她来气了,插嘴说:「吃瓜子好恶心!」对方回道:「吃瓜子关你什么事啊!」「那同性恋关你什么事!」
「我说人家同性恋,关你什么事!」对方说。
「我就是同性恋,你就说我了!」她脱口而出。
「你变态!」两个女人站起来骂。双方吵个不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笑着。
怒火消失了,「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孩子是同性恋。」她哭起来,语无伦次地说着,「不是我孩子想要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我也不知道他这样子,但是我没办法,孩子是我生出来的。他是同性恋,他不是坏人⋯⋯」
所有人都不笑了。两个女人走掉了。只剩下她,在公园继续哭着。
与很多母亲一样,得知真相的那晚,豪妈妈一夜无眠。她把凳子搬到阳台,站上去。「掉下去会是什么景象啊。是一滩肉还是几大块。」但她又想到儿子的脸,「我死了,儿子肯定也活不了。」她从椅子上爬了下来。
次日她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不吃不喝,在屋里哭得昏天暗地。朋友找不到她,通知了她的父母,物业砸开了门,看见她瘫在床上,如具尸体。朋友、亲戚、年近80岁的父母,一波波的人赶至家中。她谁也不理,所有人在她耳朵边上说话,她感觉声音很远很远的,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之前与父母吵架导致的那场少见的大哭,成了将儿子事情掩盖起来的烟雾弹。她无需解释,亲人都以为,她情绪崩溃延续于那场争执。
儿子每天给她发来同性恋的资料,她根本无心看。儿子还请她参加一个几天后在长沙举办的同志恳谈会,她觉得孩子可能被类似传销的组织控制了,不止她儿子,是许许多多的孩子。「儿子,你知道妈妈是很单纯的。这些人肯定很厉害,像黑社会的一样。」
儿子哭笑不得:「你想和人家斗,人家也不和你斗。那些都是很善良的人。」
最终她下定决心,买了一张火车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想,「反正要死我也要到长沙去死。」

协力营
那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如此不同。从事财务工作的谢秀萍来自江西赣州,她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个子女人。从事美容行业的朴春梅来自上海,她身形高大,行事雷厉风行、咋咋呼呼。银行职员董婉婉来自深圳,中学美术老师牟莉来自重庆⋯⋯几乎每人来自一个不同省份。他们有着不同口音,不同职业,不同的人生背景。2013年3月,这彼此陌生的12人(包括11位母亲和一位父亲)齐聚广州时,他们只有一个相同点,孩子是同性恋。
这群人由同性恋亲友会召集而来。这个公益机构成立于2008年,由中国首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吴幼坚与男同性恋者胡志军在广州创办(两人非母子关系)。通过各种活动与开设热线,鼓励性少数群体实现自我,促进其与家庭的理解、沟通。同志父母是核心存在。他们连接着不同世代,也连接着直人与同志社群。
敢于向父母出柜的同志本已是少数(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6年的报告,面对家庭出柜的中国同性恋者不到15%),愿意抛头露面的家长更是稀缺。早期,只有吴幼坚一人接听热线,用的就是她家电话。2012年,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吴幼坚离开了亲友会。胡志军希望更多家长站出来,他组织了「协力营」培训,取意「协聚亲友之力」。
人很难找,但凡报名就能来,好不容易才凑了12个人。朴春梅的孩子2005年就出柜了,她是亲友会的积极活动分子。董婉婉在深圳公园里每月组织同志聚会,在圈内小有名气。谢秀萍则完全是个新人。事实上,2012年12月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亲友会的存在。
儿子2年多前出柜,她「找不到和我一样的爸爸妈妈」。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做,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去向哪里。那条路很长,是她自己走完的。即便如此,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同性恋是不好的,我不能告诉别人,包括连我的父母我都不要告诉。」她甚至做好打算,等孩子苏州房子装修好,就搬去定居,尽量减少与家人、朋友的接触。
谢秀萍参加协力营,「没有带着什么学习的目的去」。在几天的培训里,她听胡志军讲LGBT的知识,再讲到按人口中3-5%的比例,中国有六七千万同性恋者。她感到疑惑,那为什么生活中看不到。胡志军解释,因为外界偏见与缺少自我认同,同志缺少社会能见度。这下,她听懂了。
家长们彼此称呼不用本名,把「爸爸」「妈妈」作为后缀。谢秀萍成了「小涛妈妈」——小涛是孩子小名儿,董婉婉成了「董妈妈」,牟莉成了「小莉妈妈」。「梅姐」比较特殊,那是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朴春梅沿用了这个名字。唯一那位男性叫做「玫瑰爸爸」。

火种
培训结束,12人回家时,每个人有个新的身份,成为各自所在省份的亲友会召集人。他们像是怀揣着一枚小小的火种,散去八方孤军作战。「儿子,妈妈决定了,想跟那些妈妈一样的,走出来做同志公益,要为你们去争取权利。」谢秀萍回来就对儿子说。
「妈妈,你准备好了没有?可能你要曝光。曝光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骂你的。」
「我不怕。」她说。
她成了江西第一个站出来做同志公益的母亲。与深圳、上海这些已经有了社群基础的大城市不同,她的工作更难开展。更何况,赣州是个三线城市,流动人口少。「我在财政局,你在劳动局,互相都认识,不敢在当地参加活动。」胡志军说。
她需要把社群聚拢起来,想到的第一个活动是聚餐。在赣州地标浮桥前,她举着一把彩虹伞拍照,以此作为海报,在网上宣传。聚会的集合点在浮桥。她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还是举着那把彩虹伞,作为相认的暗号。她对人数并无预期,来了6个人,都是年轻面孔。「哎呀,蛮少的。」她心里想。但很快,她就能感到一种孩子们与她之间那种难以言表的连接。
她深受鼓舞。第二次活动来了9个人,第三次来了13个人,逐渐增多,到后来平均每场有三四十人。志愿者也发展起来,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赣州这座小城——而不是省会南昌,成为亲友会在江西的根据地。
回到重庆的牟莉同样是从零开始。这位中学老师在成为重庆召集人之前,仅参加过一次亲友会举办的全国恳谈会,去参加协力营也一度挣扎,担心信息暴露。她通过亲友会远程协助,建立起一个同性恋QQ群,女儿帮忙拉人,一个推荐一个,逐渐扩大。
最初,她接触的都是年轻人,没有和她一样的家长。她理解,「因为年轻人还没出柜嘛,必须要出了柜,家长才出来呀。」第一个母亲——她管她叫「刘姨」,是在重庆开展工作几个月后才遇到的。那晚她当值接听亲友会热线,「刘姨」打进来求助,也是重庆人。此后,牟莉总约她一起参加活动。又过了几个月,有了第三位母亲⋯⋯
随着社群活动的开展,埋藏于内心的身为同性恋母亲的恐惧感与羞耻感,慢慢消失了。在牟莉任职的中学,她的身份也不再是秘密。她的微信朋友圈全是发同性恋话题,不分组,同事们都察觉到了,故意把话茬引起来,她承认了。大家都没说话,但这事很快传遍了学校。谢秀萍也决定让自己走出柜子。2013年6月她先是向父母出柜——出乎她意料的成功,接下来,她又向婆家的一众亲戚出柜。「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儿子给你们丢脸,从现在开始,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可以不要来往。」弟媳妇的回应颇具代表性:「作为你们父母都能接受,我们做这些叔叔婶婶大爷的,我们又凭什么不接受呢?」
2013年是一个开始,现在亲友会的协力营已经办到第七届。89个父母接受了公益培训,火种不断播下。如今亲友会在超过70个城市提供社区支持,每年办800场活动,包括各类小型分享会与规模更大、环节更丰富的恳谈会。第一届那12人,现已都退下召集人身份,交棒给年轻人,但有10位还活跃在一线。

恳谈
2018年7月21日,进入长沙恳谈会的会场时,豪妈妈是抱着极大恨意的。她一路越想越气,认为就是这些人,把她儿子的想法控制了。她到处打量,想着哪里找个棍子或者烂桌子腿,冲突发生时,手里也有个武器。
恳谈会还没开始,她坐在最后一排。她自己一人,儿子去了广州出差。那些年轻人志愿者对她特别关照,都很有礼貌,她的心柔软起来,戒备稍稍放下。每个凳子上摆着一个小册子,她拿起来翻,第一个故事就是牟莉和女儿。故事读完,戒备又放下一些。她决定坐到前排去。
恳谈会开始了,先是女同性伴侣的分享,然后是男同性伴侣分享,再来是妈妈与孩子的分享⋯⋯那些故事里有笑有泪,也有她与儿子的影子。她坐在台下,本来对儿子有些怨恨,但现在她只为他心疼。她依稀明白了,同性恋不是有病,也不是学坏了,「是大自然造成的」。
互动环节,豪妈妈主动上台发言:「儿子,你看见了,妈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我本来带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全场哄堂大笑。她想到前面发言的那位青年说,是靠着骗父母去听音乐会才把他们带过来,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让现场响起真正的音乐。
平时她是个胆小的人,但那一刻,她清唱起《我爱你,中国》。气氛变了,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我爱你」深具感染力——她心里是唱给儿子听的,台下哭成了一片。还未唱毕,她就难以控制,放声大哭。几位母亲涌上来,紧紧地抱住她。
那个晚上,她被安排和月亮妈妈住在招待所。月亮妈妈的儿子博士毕业,是耳鼻喉领域的医学专家。「比我儿子还优秀呢。」她想。博士儿子在医院里走不开,他同居的伴侣——月亮妈妈管他叫「小儿子」——这次陪在她身边。她想,至少儿子并不孤单,「他后面还有这么一大群人」。
很多家长是以求助者身份接近亲友会的,其中一些人像豪妈妈一样,带着对亲友会的不满。接热线电话时尤为明显,有人打进来就破口大骂:「把一个小孩变成同性恋你们能提成多少,为什么那么积极!」
「把你祖宗八代都给你骂到了。」朴春梅回忆,「心里头很委屈。」时常有费力不讨好的情况。有一次,对方家庭要求她带着自己儿子相见。这是个古怪的要求,她还是应承了。她先到场,那位父亲对她一通盘问,待她儿子下班过来,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好了,知道你的意图了,你是支持他们的,所以没什么好谈的。」那位父亲抬腿就走了。她气得想骂街,但看到对方儿子刚买回咖啡和甜品,端着餐盘的手在发抖。她瞬间可怜起他,赶紧让他把食物打包,去追父亲。
热线电话每晚有家长志愿者轮值接听。2014年后,更便捷的微信取代热线。求助的人多了,家长志愿者也多了。无论热线还是微信语音,提供的都不是心理咨询,更多是相互倾听与倾诉。
求助者讲自己的故事,援助者也讲自己的故事。对双方来说,这过程都像一种疗愈。你有个同性恋孩子吧,我也有。你怕吗?我也曾经怕过。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你爱他,不是吗?那个拿剪刀自残、装病抗争的常州母亲接受了同性恋女儿。那个丈夫离开他的湖南农村母亲接受了两个同性恋儿子。那个叫贺荣桂的单亲母亲,曾想控制女儿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但现在她和女儿及伴侣住在一起。
她们终于意识到,她们的孤独、惶恐、无人理解的痛苦,是孩子们都曾经历过的。网名「非凡」的妈妈忆起,孩子曾对她表示,他小时性格开朗,成年后异常内向,原因正是同性恋的身份压力,让他害怕与自卑。「如果早一点告诉我,他会少受很多苦。」她想。

改变
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离开长沙后,豪妈妈的痛苦又发作了。贵州的志愿者妈妈已经与她取得联系,将她拉到群里,她怕里面有熟人,不敢说话。最初几个月,她情绪消沉,没有和任何家长接触。她把儿子的事情说给丈夫听,他表现出对这个话题极度厌恶。发资料给他看,丈夫说:「我是不会看的,你别想给我洗脑。」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她从前是个课间走到哪里都唱歌的人,她的歌声在学校里消失了。
校长发现她的不对劲,关切地询问。她憋不住,讲了出来。但她没敢讲儿子是同性恋,只讲了丈夫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怎么过的。校长是个中年男人,拉着她的手哭了:「老大姐,你这么开朗的一个人,像个小孩一样快乐,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这么苦。」
她决定下半辈子要为自己而活。征得儿子同意后,她鼓起勇气,向丈夫摊牌离婚。「因为我从来没谈过恋爱,我不知道别人家夫妻怎么过日子的。我觉得你和儿子是一样的,说不定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求你放过我,让我自由。」她看着丈夫的眼神变得冰冷。「不行。」他故意将要求提得极高,既要房子,又要钱。
她在一众亲戚面前与丈夫撕破脸,把私事都讲了出来。他们自始至终都绕着圈说话,没有提到「同性恋」那个词。「那个人呢,事情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瞒着你一个人。」舅舅说。
丈夫搬去了老房子住。离婚僵持不下,一桩不幸的降临,令事情发生转折。那是2018年最后一天,贵阳下起了大雪,豪妈妈准备自己去重庆玩,结果刚出小区门口就摔了一跤,腿摔断了。医院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她没办法,转托一位同学打电话给丈夫。冷战多日的两人在医院里才算见了面。
两三周里她无法动弹,倒是丈夫尽心尽力地照顾。「我逃不过这个坎,我就感觉我的整个一生就这么毁了。」她看着这个男人,对他产生同情,「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历史产物。他本来就是个很懦弱的人。这么一个小人物,他生活在夹缝中,这么卑微的。」丈夫从未亲口承认过自己是同性恋,她觉得不需要去弄明白了。她不再纠结一张离婚证,她想找到重新生活的方法。
另一方面,豪妈妈在亲友会微信群变得活跃了,与妈妈们有了更多交流。她与她们一起看电影与聚餐。在她摔伤后,一群家长跑来她家里看望她。她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她开始想象,两个男人住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同在贵州的小新爸爸晒儿子小新与伴侣小涛的照片给她看,讲起他们去美国注册结婚(亲家正是谢秀萍),她觉得她也能接受。她想,同性恋家庭完全可以比异性恋家庭更幸福。她画了一幅油画,是一座开满鲜花的窗台。寓意是,这个世界给你关上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
「你老娘在前半辈子像白活了一样,成熟得太慢了。」她对儿子说。儿子嘿嘿笑。
她加了30多个微信群,群里消息一条也不错过。她听别的妈妈的故事,也听别的孩子的故事。儿子不会对她细诉身为同志的艰难,她从别人那里知晓了。通过语音直播,她也讲出自己的故事,从去恳谈会砸场的计划,到彻底对儿子的接纳。所有的那些可笑的、悲伤的经过,毫无保留。
她也被拉进了同妻的群。里面有几百人,充满着负面情绪,每天都在骂,分享「捉奸」的种种手段。她的双重身份令她对整个群体感情很复杂。她与她们同病相怜,但听到那些对同性恋群体的无差别诅咒,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感觉是在骂我儿子似的」。最终她退出了那个群。
求助者变成援助者。她抽出时间去陪伴那些新加入的妈妈们。一个妈妈在她帮助下解开心结后,给豪妈妈发了封感谢信。一个30多岁的本地男同志,她一直追踪他出柜进展,为他建立信心,不久前收到消息,「豪妈妈,我爸爸妈妈接受了。」她感到特别开心。
在家长群中,爸爸确实是稀有动物。在一次全国恳谈会,亲友会半带调侃地搞了个《爸爸去哪了》的访谈。如果你问起妈妈,她们更愿意给出一种外交辞令式的答案:爸爸们太忙了。
她们是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一代人,但她们在努力追赶这个疾驰的时代。为了与年轻人社群连接,许多母亲学会了使用直播软件,YY、一直播、抖音、blued,什么流行就用什么。为了理解孩子的真正需求,安徽的利利妈妈报考了心理咨询。「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们谈过性。」董婉婉说,她在学习性知识。
同性恋者的母亲,成为她们共同的名字。她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广州的妈妈们,会定期组织喝早茶、自驾游。成都的妈妈们组织了合唱团。厦门的小炜妈妈成立了一个有百余人参与的艺术团。为了更美地完成旗袍走秀,妈妈们穿上了高跟鞋,学着涂指甲,接上假睫毛。从事美容行业的朴春梅顺理成章地成为领衔化妆师。
但这个群体的存在,不只是个情感互助小组,她们也希望将声音送到社群之外。她们进到大学开座谈会。她们走进公园的相亲角,为孩子们找对象倒是其次任务,她们希望孩子们被社会看见。她们在朋友圈里一遍遍地发起亲友会的公益募款。
身为同性恋者的母亲,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选择。这个事实很早即发生,早在她们还未能认识彼此的时候,早在她们真正懂得「同性恋」这个词之前。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给予,如何去爱。你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可以走左边,也可以走右边。
6月底,亲友会组织了一场前往越南的邮轮旅游,上千位同性恋者与家属登上了船。几百个妈妈来了。豪妈妈与儿子也在其中。
那天早上不到5点,母子俩跑上甲板。茫茫大海上,只有这一艘船。甲板上零星几个人。旁边一对同志情侣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谁也没有说话。儿子举起一条细细的彩虹绸带,绸带迎着海风飘扬。妈妈面容沉静,目视远方,手攀上儿子的肩膀,轻轻地,缓慢地拍着。她感到幸福。太阳还躲在云后,天正慢慢亮起来。